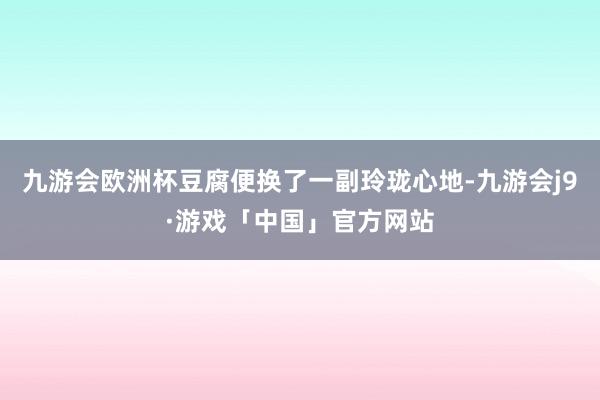
本文作家:食戟社
中国东说念主对豆腐的爱,是刻在本色里的。这份爱,越过了地域的天差地远,在每一方小小的豆腐里,齐藏着一方水土的本性与一个民族的聪慧。
在东北的极冷里,豆腐是铁锅边上最诚挚的暖意。大块的豆腐和白菜、粉条、猪肉在粗莽的铁锅里咕嘟着,汤汁浓郁,热气蒸腾。炖煮后的豆腐,吸饱了肉的丰腴与菜的清甜,变得蓬松而多孔,用筷子夹起时颤巍巍的,进口是滚热的、塌实的无礼。它像极了关东的汉子,外在朴实,内里却吸纳了百家精华,暖了肠胃,也暖了漫长的冬日。
而到了江南,豆腐便换了一副玲珑心地。杭州的西湖边,总共“蟹粉豆腐”,将豆腐的嫩滑与蟹黄的鲜醇进展到极致。那洁白的豆腐,在淡雅的瓷羹中,如初雪覆地,金黄的蟹粉点缀其间,是江南水墨画里一抹亮丽的暖色。进口即化,鲜气在舌尖缭绕不去,那是文东说念主骚人笔下的致密,是烟雨楼台中的一缕缓和。
伸开剩余69%若说江南的豆腐是大师闺秀,那么四川的豆腐即是江湖儿女。麻婆豆腐,一听名字便觉大意生风。白嫩的豆腐丁,在红亮的辣油与深色的肉末中翻腾,披着孤苦密密匝匝的花椒粉。一勺舀起,麻、辣、烫、鲜、香、酥,六味一体,短暂点火味蕾。它不讲含蓄,只求逍遥淋漓,豆腐在那顽强的调味中,一经保捏着内心的柔嫩,这是一种至柔克刚的玄学。
岭南之地,矜重的是“食不厌精,脍不厌细”。那边的豆腐,常与海鲜为伍。总共酿豆腐,将鲮鱼肉茸或虾肉细细剁碎,玄机地酿入一方方小小的油豆腐或嫩豆腐中,或清蒸,或焖煮。豆腐的豆香与海鲜的甘甜相互浸透,清淡中见档次,鲜爽中见功夫。它体现的是广东东说念主对本味与口感的极致追求。
更不必说,在湘西的农家,有黑豆制成的柴火豆腐,烟熏火燎,别具风姿;在云南的建水,豆腐被烤得金黄饱读胀,蘸着椒盐辣子,是商人街头最诱东说念主的焰火气;而在安徽的徽州,那资格了漫长发酵的毛豆腐,长着密致的绒毛,煎烤后异香扑鼻,是腹地东说念主才懂的、化陈腐为神奇的味觉密码。
你看,从北到南,豆腐不错是主食,是小吃,是宴席上的大菜,也不错是清修之东说念主的斋饭。它不错是任何面容,符合任何口味。它像水相似,随物赋形,俟机劫掠地融入中国饮食的每一个边缘。
为何咱们如斯醉心豆腐?大要,是因为它像极了咱们这个民族的底色——朴素,包容,而又富于韧性。它自己滋味清淡,恰似一张白纸,却能包容山川湖海的滋味,与任何食材搭配齐不显突兀。它质量优柔,却能接管煎、炒、烹、炸、炖、煮、熏、酿的千锤百真金不怕火,在猛火与热水中树立各式滋味,千种风情。
这洁白的一方,是中国东说念主餐桌上的“和事佬”,团结着南北东西的口味;亦然咱们文化顾忌里的“条约数”,无论身在何方,一碗热腾腾的豆腐下肚,即是回到了故我。
是以,不同处所的豆腐服法虽然天差地远,但那份深植于基因里的认可与喜爱,却弥远如一。咱们爱的,早已不只是豆腐自己,更是它背后所承载的那份任性的聪慧、广宽的胸怀九游会欧洲杯,以及那历经磨练,却弥远纯净、温润的东方灵魂。
发布于:吉林省